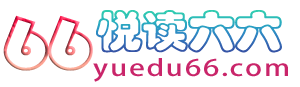
六月七日的清晨,天光像被打翻的牛奶,慢悠悠地漫过市一中的红砖墙。
吴朋站在考点门口的梧桐树下,校服后颈的标签磨得皮肤发痒,
手里的准考证被汗水浸出深浅不一的褶皱。他数着地上被阳光切割出的光斑,
第七个菱形光斑晃过眼时,那辆熟悉的黑色奔驰果然如前世般碾过积水潭,停在警戒线外。
车门打开的瞬间,吴亮被簇拥着走下来。定制款**版球鞋踩在水洼里,
溅起的泥点像精准计算过般,落在吴朋洗得发白的白球鞋上。“哥,紧张吗?
”吴亮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,手腕上的百达翡丽表链在晨光里划出冷光,
“张阿姨说你昨晚学到三点?别熬坏了脑子,反正也考不过我。”周围响起细碎的哄笑。
吴朋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,铁锈味从喉咙里漫上来。
他记得这个场景里的每一个细节:吴亮衬衫第二颗纽扣松了线,
赵慧兰手里保温桶的提手缠着蓝布条,甚至围观人群里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女生,
此刻正偷偷用手机对着他们拍照——前世就是这张照片,
被配上“真少爷黯然失色”的标题,在本地论坛飘了三天。“吴朋,过来!
”养母赵慧兰的声音穿透人群,她把保温桶往吴朋怀里塞,眼神却黏在吴亮身上打转,
“你看你弟弟多精神,衬衫熨得笔挺,你也学着点体面。”吴朋没接保温桶。
茶叶蛋混着桂皮的香味钻进鼻腔,是他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前世他就是被这香味勾着,
伸手去接的瞬间,吴亮假装帮忙扶桶,趁机抽走了他裤兜里的准考证。
等他在考场门口被拦下时,语文考试已经开始了四十分钟。“阿姨,我帮你拿吧。
”吴亮抢过保温桶,亲昵地挽住赵慧兰的胳膊,
指甲上还留着昨天做的水晶甲——那是吴朋去年生日时,
亲生父亲吴建国答应要带他去做的,最后却出现在了吴亮的手上。“妈说早餐要吃清淡点,
我给哥带了进口牛奶。”他从背包里掏出银灰色包装盒,外文标签刺得吴朋眼睛发酸。
“还是亮亮懂事。”赵慧兰笑得眼角堆起褶子,伸手替吴亮理了理领带,
完全没注意到吴朋攥得发白的指节。吴朋的目光越过人群,落在公告栏的考场分布图上。
前世就是在那里,
他看到自己的考场被改成了最远的实验楼302室——后来才知道,
那是吴亮托教务处主任偷偷改的。这一次,他提前三天就去教务处核对过三次,
把高一(3)班的教室编号刻在了脑子里。“进场了。”监考老师举着牌子走过,
吴朋跟着人流往前走,路过吴亮身边时,故意肘弯一拐撞在他胳膊上。
牛奶盒“啪”地掉在地上,乳白色的液体在柏油路上漫开,像摊没擦干净的眼泪。
“你干什么!”吴亮的尖叫刺破晨雾,他跺着脚跳开,**版球鞋沾了点奶渍,
“你是故意的!”“抱歉。”吴朋的声音很轻,却带着冰碴子,“手滑。”他没回头,
径直走向教学楼。身后传来赵慧兰的怒骂声,还有吴亮气急败坏的叫嚷,
但这些都没能拖住他的脚步。
教学楼门口的电子屏显示着“距高考开始还有20分钟”,红色数字像跳动的火焰,
灼烧着他的眼球。考场里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,扬起粉笔灰混着旧书本的味道。
吴朋坐在靠窗的位置,第三次检查准考证上的照片——那是他高二拍的,
左脸颊还有颗没消的青春痘。前世被调换的准考证上,照片是初一的寸照,发型都不一样,
可当时慌了神的他竟然没发现。语文试卷发下来时,吴朋的指尖在颤抖。他深吸一口气,
强迫自己盯着卷面。第一道选择题考字音,
四个选项里“绯闻”的“绯”总被人读错第三声。前世他在这里纠结了三分钟,
最后还是选错了。这一次,他笔尖顿了顿,毫不犹豫地圈了正确答案。
阅读题考的是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。吴朋的笔尖悬在半空,
眼前突然闪过养母的脸——十岁那年他出水痘,养母背着他走了三站地去医院,
路过城郊的荷塘时,也是这样的六月,荷叶上的露珠滚进水里,像碎掉的星星。他甩了甩头,
把这些画面赶出脑海,专注地在“月光如流水一般,
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”这句话下划了波浪线。作文题是“初心”。
吴朋写下这个词时,钢笔漏了滴墨水,在纸上晕开个小团。他想起十岁那年,
亲生母亲林婉来学校看他,偷偷塞给他一个缠红绳的银镯子,冰凉的金属贴着掌心,
她说“等你考上重点高中,妈妈就接你回家”。那镯子现在还在他的枕头下,
被体温焐得温热,内侧刻着的“婉”字已经磨得快要看不清。“还有十五分钟。
”监考老师的声音像警钟。吴朋迅速检查完试卷,抬头时正好对上斜前方吴亮的目光。
对方冲他做了个口型,虽然隔着三排座位,吴朋还是看懂了——“等着瞧”。
前世的英语考试,吴亮趁着交卷混乱,偷偷拔了他的耳机线,让他错过了最后五道听力题。
吴朋摸了摸桌肚里的备用耳机,那是他用攒了半个月的午餐钱买的,藏在笔袋最底层,
耳机线缠着三圈红绳做记号。中午在考点附近的面馆吃面,吴朋特意选了靠窗的位置。果然,
他看到吴亮和两个染着黄毛的男生在街角说话,其中穿黑T恤的男生他认识,
是高三(七)班的混混阿强,前世就是这两个人把他堵在实验楼后的小巷里,
抢走了他的钱包,还把他反锁在杂物间,耽误了下午的英语考试。“老板,再加个蛋。
”吴朋把剥好的蛋壳扔进垃圾桶,心里已经盘算起应对的法子。
他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塑料哨子——那是他初中当体育委员时发的,
吹起来能穿透三层教学楼。下午考英语前,吴朋故意绕到实验楼后面的小巷。刚走到转角,
两个黄毛就跟了上来,阿强手里还攥着根磨尖的木棍。“小子,识相点就把准考证交出来。
”阿强晃着木棍,唾沫星子喷在吴朋脸上,“亮哥说了,给我们五百块,
让你‘不小心’摔断腿。”吴朋后退一步,背靠着斑驳的墙壁:“他给你们五百,
我给你们一千,说出是谁指使的。”黄毛愣了一下,随即恶狠狠地说:“少废话!
”就在他们扑上来的瞬间,吴朋猛地吹响了脖子上的哨子。尖锐的哨声刺破午后的寂静,
惊得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。巡逻的保安循着声音跑过来,两个黄毛见状不妙,撒腿就跑,
却被保安逮了个正着。“同学,没事吧?”保安扶着他站起来,吴朋注意到不远处的树后,
吴亮的身影一闪而过,白色衬衫的衣角还露在树影外。英语考试顺利结束。
听力部分的最后一题,吴朋听得格外清楚,那是段关于志愿者活动的对话,答案选C。
交卷时,他看到吴亮盯着自己的答题卡,眼神里满是错愕,仿佛在看什么不可思议的事。
第二天考数学,吴朋提前半小时就做完了试卷。他趴在桌子上,看着窗外的云飘过教学楼顶,
想起前世数学只考了78分,吴亮拿着142分的成绩单在他面前晃,
说“基因这东西,改不了”。那时他还不知道,吴亮的试卷是抄了前排学霸的,
监考老师是他舅舅的老同学。理综考试是吴朋的强项,也是吴亮最薄弱的环节。
最后一道物理大题考电磁学,吴朋只用了十分钟就解出来了,而斜前方的吴亮还在咬着笔头,
额头上渗着汗,草稿纸揉了一团又一团。交卷的**响起时,吴朋清楚地看到,
吴亮的试卷上,那道18分的大题还是空白的。走出考场的那一刻,
阳光刺眼得让人睁不开眼。吴朋站在教学楼下的公告栏前,看着陆续出来的考生,
突然觉得无比轻松。他知道,无论结果如何,这一次,他没有留下遗憾。
赵慧兰和吴建国来接他们时,气氛有些尴尬。赵慧兰拉着吴亮的手问东问西,
吴建国则拍拍吴朋的肩膀,欲言又止。“晚上回家吃饭吧,你张阿姨做了红烧肉。”最后,
他还是说了这句话。吴朋摇了摇头:“我回养父母家。”他转身走向公交站,
没看到吴建国眼里一闪而过的愧疚,也没看到吴亮嘴角勾起的得意笑容——吴亮的计划,
还没结束。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,清华北大的招生海报在夕阳里泛着金光,
吴朋盯着那行“等你很久了”的标语,握紧了书包带。等待成绩的日子像南方的梅雨季,
潮湿而压抑。吴朋住在养父母家,每天帮养父修理自行车,陪养母去菜市场讨价还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