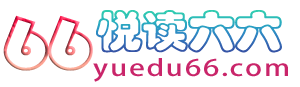
关山月听完,却只是歪了歪头。
“我当是多大个事儿呢。”
她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别人家的闲事。
“资本家后代咋了?”
她双手叉腰,往前走了一步,一股带着皂角和山风味道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“我又没见过资本家啥样。”
在21世纪,她就是最大的资本家。
沈砚清猛地抬起头,不敢置信地看着她。
关山月被他那副样子逗笑了,她大大方方地一指自己。
“再说了,你也不看看我。”
“爹娘早没了,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。”
她的目光坦然,带着一种山野里长大的,不管不顾的野性。
“200来斤呢,屯里半大小子都说我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”
她顿了顿,嘴角那丝算不上传善的笑意又浮了上来。
“真娶我,怎么算都是你吃亏。”
她看着他那张呆掉的脸,心里觉得好笑,挥了挥手。
“行了,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“我还不至于赖上一个被我捡回来的。”
“不勉强你。”
她说完,转身就想去灶房烧水。
“没有勉强。”
身后,一道清越却带着颤抖的声音响起。
关山月脚步一顿,缓缓回过身。
沈砚清依旧跪在地上,但他的背脊却挺得笔直,像是寒风中绝不弯折的青竹。
那张俊美无俦的脸上,不再是惊慌失措,而是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。
“你救了我的命。”
他看着她,眼睛里像是燃起了一簇小小的、微弱的火苗。
“我身上,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钱财,地位,名声,全都没有了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将那句话说了出来。
“你若真的不嫌弃,沈砚清......我......我愿意的。”
这下,轮到关山月僵住了。
她嘴巴微张,看着地上那个一脸决绝的男人,脑子里嗡嗡作响,像是钻进了一窝马蜂。
这都什么跟什么?
她就是随口开了个玩笑,想吓唬吓唬这个寻死的俊秀书生。
怎么他就当真了?
还......以身相许?
关山月活了十八年,头一回碰上这么离谱的事。
“你......你凭啥啊?”
她憋了半天,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,问了个最实在的问题。
沈砚清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,白皙的脖颈上浮起一层不自然的薄红。
他的视线落在地上开裂的泥缝上,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。
“我......我看了姑娘的身子。”
“男女有别。”
沈砚清的头垂得更低了,声音却固执得像块石头。
“看了,便要负责。”
关山月彻底说不出话了。
她看着这个迂腐得可笑的男人,心里那点戏谑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关山月是知道男人的劣根性的,在现代,她接触到的男人非富即贵,那些人私生活有多乱,她也常有耳闻。
而且,现在这个年代,她也了解一些。
这个年代,虽然大部分还是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但还是提倡自由恋爱,所以很多年轻人婚前会滚在一起,不负责任的渣男也挺多。
他居然因为看了女人的身体,就想负起责任来?
这担当......
他不是资本家大少爷吗?婚恋观这么保守?
负责?
她长这么大,连她爹都没跟她说过要对她负责。
倒是她这身子的爹临死前,拉着她的手,翻来覆去就一句话,说对不起她,没给她找个好婆家,怕老关家到她这就断了根。
断了根......
她其实也不在乎断不断根的,可是从这身体的记忆来看,老关生前对她挺好的,有一口吃的全给了她,所以也在这缺衣少穿的年代,把她这身子养得如此白白胖胖的。
关山月的目光,不由自主地又落回沈砚清那张俊美得不像话的脸上。
屯里人都说她二百来斤,又虎,一辈子都嫁不出去。
可要是......
要是真跟他成了家,生的娃,那得好看成啥样?
这是绝对的基因优势啊。
一想到这,关山月那颗被山风吹得粗糙的心,忽然就软了一下,脸颊也莫名其妙地发起烫来。
她清了清嗓子,故作镇定地背过身去。
“行吧。”
她的声音听起来依旧大大咧咧,却藏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羞涩。
“那......那明天我就去找村长开介绍信。”
沈砚清没想到她答应得这么干脆,微微一怔,随即心里涌上一股复杂的滋味。
“那......彩礼......”沈砚清他张了张嘴,刚想说彩礼。
话到了嘴边,却又咽了下去,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块滚烫的烙铁。
在沪上,他这个出身的人家娶妻,那是一等一的体面事。
聘礼单子拉出来,长得能从弄堂头铺到弄堂尾。
别说寻常人家都稀罕的“三转一响”: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收音机。他家要备的,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小黄鱼,表得是瑞士运来的表,是整匹整匹的英国洋布,是各种古玩瓷器名画,是拍卖行的玉器珠宝首饰,还得在霞飞路备下一栋小洋楼当新房......
那是对女方家的尊重,也是沈家的脸面。
可现在呢?
他沈砚清,还有什么?
脸面?尊严?早就在那些冰冷的唾骂和无情的批斗中,被踩进泥里,碾得粉碎了。
他有什么资格,去娶一个救了自己性命的姑娘?让她跟着自己这个一无所有的“资本家后代”,在这穷山沟里抬不起头来?
心口一阵尖锐的刺痛,他攥紧了拳,指甲深深陷进掌心。
“姑娘......”他终于找回了声音,却沙哑得厉害,“我......。”
可话还没出口,就听见关山月抢先开了口。
“那个......”
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惴惴不安。
“你要多少彩礼?”
沈砚清猛地抬头,彻底愣住了。
?
他要多少彩礼?
关山月没看他,自顾自地盘算着,声音越说越小。
“我......我手里存的钱不多,不过有二百斤粮票,还有些布票,不知道够不够......”
沈砚清的脑子“轰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他终于明白了。
她这是......要他入赘?
一股巨大的羞耻感瞬间席卷了他全身,从脚底板一直烧到天灵盖。
他一个大男人,怎么能入赘,还拿女人的彩礼?
可他又能怎么样呢?
他是下放来改造的资本家后代,一个随时可能被拉去批斗的黑五类。
他身上所有的钱加起来,不到十块。
他拿什么娶她?拿什么给她一个家?
他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。
入赘......
似乎是他唯一的选择了。
他看着关山月真诚又带着点紧张的侧脸,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算计,只有怕自己拿不出足够“彩礼”的担忧。
沈砚清心头一颤,所有的羞窘和不甘,都在这一刻化成了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遇上这样的女人,他认命了。
他的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,最后落在了门后桌角上,那里挂着三只冻得邦邦硬的野兔子。
“彩礼,我不能要。”
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清越,只是带了些沙哑的疲惫。
“就......就要那三只野兔吧。”